Digital Activism and the Populist Surge of the Men’s Rights Movement
文 / Sara Liao(廖雪婷)
翻译 / 阮璐欣
校对编辑 / 廖雪婷、郑叶颖、叶云鹤
大家好,感谢网络社会研究所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的演讲将重点关注男性权益运动,或者您可以简单地将其视为男权运动。这不是一项完整的研究,而是我在反思和撰写有关数字行动主义和中国厌女文化时的一些观察和想法。这里有很多初步的想法,其中一些部分我可能没有真正考虑清楚。如果您有任何反馈、意见和建议,帮助我继续前进并更深入地思考此处将讨论的问题,我将不胜感激。
我想从最近发生的一件引起全中国关注的事件开始,中国最大的电商促销活动“双十一”即将来临,很多电商平台几乎在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前就开始推出促销活动。许多平台选择与明星合作,其中最大的电商平台之一就是京东。然而,京东却因此陷入了公共关系危机。京东最初与几位明星签署了协议,其中包括一位著名的单口喜剧(或称“脱口秀”)演员杨笠,以宣传该平台的“双十一”购物活动。该活动于2024年10月14日启动,但杨笠在启动仪式上的出现很快激怒了许多京东的男性顾客,他们涌入该品牌的社交媒体账号,包括微博等平台,发表评论以表达愤怒。
杨笠是中国新一代女性喜剧演员的领军人物之一,她以嘲讽男人的自负而闻名。2020 年末,她在一次网络节目演出中以“为什么男人看起来那么普通,却可以那么自信”1为噱头,讽刺了男人的自负,引发了热议。这个噱头本身变成了关于男人和他们的自负的笑话,并创造了一个新词“普信男”,意思是普通但自信的男人。这种基于性别的抨击使她成为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许多人指责她反男人、厌恶男人,甚至煽动对男人的仇恨。而京东以销售电子设备而闻名,根据市场调查,男性实际上占据了该平台用户数量的 60% 以上。
在社交媒体上,你会看到很多重复“普信男”梗以攻击杨笠的用户,认为她在此次活动中为京东代言是不恰当的。还有一些人指责该平台说,你们收男人的钱,给杨笠代言费。有些京东会员甚至要求京东退还京东 Plus 的订阅费,这是一个类似于亚马逊 Prime 的会员计划。因此,京东很快就在最初宣布与杨笠合作的四天后回应:10 月 18 日,该公司从其各个平台的频道上删除了所有与杨笠有关的宣传帖子,甚至还发布了一份道歉声明。道歉信上写道:如果部分喜剧演员参与京东双十一活动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我们诚挚道歉。并且还表示,公司与上述喜剧演员没有进一步的合作计划。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杨笠删除了自己微博中与京东双十一活动相关的帖子。实际上,即使在京东与杨笠结束合作关系后,这场争议仍在继续发酵。但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已足以说明我的观点。我对追逐此事件的后续发展并不感兴趣,而是想指出在这场争议中目前出现的一些有趣的与本主题重合的部分。
杨笠成为京东双十一代言人的争议对于中国网民而言并不陌生,这是一种关于性别对立的叙事。甚至可以说,性别对立成了杨笠作为名人身上的一个标签或符号。尽管她从未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也从未直接宣传过任何性别平等问题。平心而论,杨笠早已习惯了争议。2021 年早些时候,在英特尔中国的笔记本电脑广告中出现了她的身影,作为回应,大量男性用户主张抵制该公司作为反击,指责该公司与侮辱男性的女性合作。同年晚些时候,杨笠在微博上与豪华汽车制造商奔驰一起出现在一个短视频中,同样招致了强烈批评。而为了回应这段视频,一些自定为男性的网民攻击杨笠,他们认为这位喜剧演员是挑起男性仇恨和性别对立的关键人物,甚至呼吁抵制奔驰。因此,在所有类似事件中,性别对立已被大量引用,以指责那些煽动仇恨或挑起敌意,甚至仅仅是讨论这些性别问题的人。在网上搜索“性别对立”时,无论在哪个平台上搜索,可能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其中涉及到的问题包括:得体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约会文化、亲密关系、婚姻,有时也包括性暴力、生育权、反女性主义。此外,你可能还会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阴谋论,指责外国干预中国的性别问题。
但我并不太关心“性别对立”作为一种话语究竟包含和涵盖了什么,而是试图思考这一话语凭借其在公共文化领域——尤其是数字空间中的显著性、可见性和流行性——可以实现什么。性别对立的叙事实际上逐渐演变成了一种主流的、甚至是主导性的文化套路(cultural trope)2,它使任何被认为破坏性别规范的事物陷入停顿,尤其是那些与异性恋传统(heteronormative conventions)和父权资本主义有关的事物。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还会发现,性别对立充当了恶毒的厌女症和反女权主义言论和行动的稻草人,目的是破坏进步政治。这种围绕性别对立的话语叙事本身是技术、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交织的结果,被一些人、一些机构甚至一些媒体用作武器,主要针对妇女和女权主义者实施攻击和暴力。这也是我开始了解男性权益运动的起点。
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技术的发展曾一度备受赞誉,被誉为社会底层的民主工具。多年来,我们确实看到世界各地的草根阶层如何利用丰富的数字资源组织动员,通过各种平台开展创造性实践,并尽力培养进步的运动和政治文化。但与此同时,商业利益和反动政治议程在信息与传播技术发展中的渗透,也打破了我们对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乌托邦式的想象。数字技术、平台经济、父权的文化习俗、监管要求甚至媒体用户的实践,所有这些集合在一起,催生了一系列非常强大和具有压迫性的数字话语和行为,其中许多会被归类为性别歧视、种族主义、仇视同性恋或仇外心理等。
因此,如果我们同意技术是我们社会的一面镜子,它在被塑造的同时塑造着我们所处的文化。那么,技术不仅促进了融合、团结和多样性,同时也同样导致了分歧、不和谐和狭隘主义(provincialism),而这些则会严重阻碍关于解放、自由和社会正义的进步政治。在当代文化和政治格局中,男性权益运动与数字媒体和网络反动文化(reactionary culture)(也可以说是亚文化)的兴起密切相关。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术语是“男性圈层”(manosphere),或者准确地说,是“数字男性圈层”(digital manosphere)。它描述的是多样化但又支离破碎的网络社区,包括那些网站、博客、视频博客、不同类型的社交媒体账户、论坛、维基百科页面或播客,所有这些都在共同宣扬反女权主义和厌恶女性的言论和文化。这些网络社区可能明确或不明确地推动男权运动,但其重点是在批判或曲解女性主义的基础上,用基于反动的性别角色来构建男性身份。因此,我在这里展示了一些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的男性圈层的例子,它们也代表了我在深入研究男性权益运动或实践时一直关注的一些案例或社交媒体资源。
其中,名为“Morpheus红丸主义”的社交媒体账号,是中国受众了解男权运动流行思潮和组织实践,并向西方学习的重要信息枢纽。它从男权社群的角度翻译出版了许多教学资源,例如“搭讪艺术家”(pickup artist,台湾翻译为“把妹达人”,大陆俗称PUA),红色药丸(The Red Pill)、男人自行之路(Men Going Their Own Way),中文译为 “米格道”(MGTOW)3和“非自愿单身者”(incel)。
在微信公众号平台上,有一个名为“觉醒者围炉”的账号,其发布的许多信息是对本土性别问题的分析和评论。这些分析和评论通常采用的是讲男性受害者化的故事讲述方式,结合反动和反女性主义的态度和言论。在中国的数字男性圈层中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事件,即孙吧事件。孙吧是百度贴吧上一个流行的亚文化论坛,其数百万男性用户在该论坛上发布和交流关于女性的图片和信息,以一种恶毒而暴力的恶搞、诽谤、嘲弄和网络欺凌的方式对普通女性和女权主义者进行猎巫。在巨大的反对声浪下,百度删除了这些曝光帖,但该论坛本身仍然存在。还有一个例子:一些男权倡导者在维基百科创建了一个子页面,称其为“石头百科”。这是一个站在男性立场上记录中国许多性别事件的网站。因此,它侧重于收集部分性暴力事件的诬告案例、男性厌恶案例、对男性气质的攻击或男性在家庭和公共领域的受害情况等等。创始人认为,这是男性试图夺回话语权、改写历史的标志(男性圈层又称其为“岁月史书”)。所以,这是“他的故事”(his-story)。男性圈的论坛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内容和主题也各不相同,但从根本上说,它支撑、支持和塑造了当代男性权利的倡导及其可能带来的暴力行为,折射出了在跨国背景下更广泛的社会现象。
在我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令我惊讶的是,男性权利的论述和倡导实际上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一些学者将其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当时英国、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人权活动家和团体都曾参与其中。他们关注一系列影响男性和男童的问题,如男性无家可归、心理健康、暴力指控、法院的偏见、自杀、儿童监护权、国家或社区对男性住房问题的低资助、教育表现以及主流文化中的歧视等。美国学者认为,提高男性意识及其权利的论述和实践应被视为更广泛的普遍解放政治的一部分。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形成的大致情况一样,在这种解放政治中,主要思想并不是简单地促进男性权利,而是旨在使男性和女性共同受益。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这种男权话语已经消失,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关于男性解放的话语在其内部分化为两条不同的路线。其中,较为保守和温和的一派成为了反女权主义的男权运动(Men’s Rights Movement),简称为 MRM。而较为进步的一派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更为深刻的运动,他们使用我们在许多女权主义运动中常见的语言,并承诺解决性别关系和权力问题。
前者作为男性解放运动中较为保守和温和的一翼,在当今获得了更高的可见性,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易用性(affordability)以及数字平台的兴起。2009 年,男权活动家保罗·艾伦(Paul Allen)创办了一个名为“男人之声”(A Voice for Men)的男权网站。第二波”这一术语的使用当然与19世纪晚期至21世纪早期的女权主义或女权主义运动的浪潮无关。根据“男人之声“网站的使命声明,这一术语“表达了当下激增的(男权)活动,这些活动尤其独特之处,同时与之前的运动浪潮紧密相连。” 这种承前且独特的运动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包括国家内部和跨国网络的建立、参与者在性别、种族、阶级和性取向方面的包容性,以及总体上反女性主义、反女性中心主义和反男性憎恶的立场。
但即便是这种MRM也呈现出一个光谱。一些人呼吁“和平、非暴力的运动”,其活动的核心是“改变文化叙事,而不是游说官员修改法律”——他们认为法律的设立本身就对男性存在偏见。而另一些MRM成员则更多地与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包括阴谋论和极右翼思想,并庆祝和推动暴力行为,例如大规模枪击中的残暴杀害女性(femicide)以及基于性别的性犯罪。与MRM相关的许多恶毒和暴力话语及行为,主要出现在近年来的数字社区中,例如前面提及的incels以及其他特定文化背景中的群体。
总体而言,我们看到学术界对男权运动作为一种数字亚文化的分析有许多新的研究,但它仍然是一个研究不足的领域,尤其是在中国。因此,我确实找不到太多文献讨论作为数字亚文化或数字环境中的男性权益倡导问题。中国最受欢迎的男权博客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 Morpheus 红丸主义。他,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就称其为 “它 ”吧——大约是在 2020 年底,它开始在流行的视频分享网站哔哩哔哩上传视频。在我关注的所有社交账户中,没有任何关于男权的话题、视频或任何形式的讨论早于 2020 年4。因此,根据我目前收集到的有限信息和资料,我谨慎地初步认为,男性权益倡导作为一种亚文化开始在数字媒体上形成或显现的时间大约在 2020 年。而我之前提到的喜剧演员杨笠也是在这一年创造了“普信男”这个词,并在此后引发了大量的热度和争议。这可能是一个巧合,但也可能是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积累的反动的反话语爆发了,并逐渐发展和演变成这种男权主张和一系列压迫行为和话语。男权活动家所创造的内容和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同行以及韩国男权运动的启发。男权运动的许多理论和经验资源都来自红色药丸和米格道,它们真正关注的是意识的提升和与女性普遍分离的生活。
于是,前面提到的女本位主义的思想被引入中国。他们翻译了许多男权活动家的 YouTube 视频,并将它们搬运到亚文化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上。女本位主义作为一个概念,是过去男权运动中流传最广的主题和话题之一,指的是在历史或实践中对女性的主导性或排他性关注,这是一种单纯从女性角度、从女性立场出发的观点或叙事。他们在男权运动中不断辩论或提醒说,我们需要重新夺回书写我们历史的话语权。因此,反女本位主义是男权运动的基础。我认为韩国对此影响很大,一方面是因为中韩两国在父权制和社会等级制度的性别政治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女权主义和韩国女权主义之间深入有效的交流,确实激起了这些国家男性的焦虑和愤怒。特别是近年来,有一套强大的女权主义实践模式从韩国传播到中国,呼吁女性超越以男性为中心并使男性受益的活动,包括不结婚、不生育、不谈恋爱、不与男性发生性关系、不消费厌恶女性的产品,拒绝偶像文化、拒绝宗教信仰、拒绝任何被性化和剥削女性的审美标准等等。因此,韩国和中国的男性都认为,他们被歧视性的当成了性压迫、强奸文化和性别暴力的罪魁祸首。学习韩国男权运动的反击方式,可以为中国男权活动家提供评估其数字战略的线索,特别是在组织、动员和有效打击他们认为非常以女性为中心或只有利于女性的言论、政策和做法方面。
总的来说,我观察到男权倡导者的两种主要做法,一种是在数字经济中恰当地利用微型名人或微型企业家的整体理念,创建另类媒体,从不依赖任何主流媒体,并提供以男权为中心的内容。这种做法就像任何希望拥有影响力的文化的人一样,通过提供信息、发表评论、倡导和与追随者进行讨论,在受众中建立信誉和信任。这一套做法,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让人觉得男权倡导既是失败者文化(loser culture),又是一门生意。另一种做法则体现在他们创作和传播的内容中,以及他们与自己的受众建立的社群和关系中。在这些内容和社群中,男权活动家或倡导者试图为自己和受众提供一个非常具体的社会身份,将自己和观众呈现为反主流文化中的社会弱者。这种社会弱者叙事通常利用两种道德或话语资源,其一是民族主义,其二是所谓的草根和反精英主义,或反资本主义。我们可以从中国数字空间的任何公开讨论中获取这两种符合中国式政治正确与道德标准的论述。
在男权宣传中使用这两种资源几乎完全符合荷兰政治学家卡斯·穆德(Cas Mudde)对民粹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定义:争论发生于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之间。在中国的男权倡导运动中,就是作为社会底层的纯洁男性与腐败的女权主义者,或以消费主义为导向的坏女人之间的对抗。于是,倡导男权就成了代表人民普遍观点的政治立场。同样是意识形态,它确实需要依赖更宏大的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才能发挥作用。在男权运动的许多案例、论述,以及衍生的后期视频中,都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观察到,倡导男性权利往往与将女权主义与外国干涉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也让我们注意到许多所谓的爱国博主和有影响力的人,他们以民族主义和反女权主义为中心进行微创业。我并不是说他们都是男权倡导者,但这和男权活动家利用这些话语资源来建立自己的叙事和身份并进一步与其社群共享的方式十分相似。我们或许可以从杨笠-京东的案例中看到,长期以来,杨笠一直被指称与所谓的西方力量有关,因为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了她整个职业生涯中的噱头和争议,而男权倡导者则将这些争议视为对杨笠及女权主义的民族主义攻击,他们通常还引用性别对立的话语和套路。
这里的反女权主义并不是沿着继续叙述男性受害故事,或者女权主义者或女性如何剥夺男性权利的逻辑,而是试图使用民族主义语言,将女权运动与旨在分裂中国、威胁中国人民和社会稳定或安全的外国干涉主义结合起来。这两种话语资源在中国语境中都是政治正确的,也得到了党和国家以多种不同方式的明示和暗示。维护这种道德叙事即获取话语资源,媒体平台通过其内容监管和治理也体现了这一点。微博、微信、哔哩哔哩、知乎、虎扑等平台在为公众提供讨论空间的同时,也在努力平衡意识形态和商业利益。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提出的,有毒的男性圈层在中国高度可见,或者就是我所说的厌女症平台化。在这里厌女症不仅是一种表达形式或活动,而且是一种治理形式,一种基于平台的技术驱动治理:科技公司、媒体机构、数字平台和媒体用户非常明确的同意和合作,同时借用如父权资本主义、家长制下的专制主义、外国干涉主义、反女权主义等意识形态共同形塑平台内容、影响公众讨论。因此,男权倡导可能是国家-市场综合体(state-market complex)中此类现象的最新迭代。我在这里使用的国家-市场综合体这一概念是受军事-娱乐综合体(military-entertainment complex)的启发,其分析最常见的用途是军队与娱乐业之间的互利合作。我引用这个类比来说明数字技术、平台经济、父权文化、国家监管和媒体用户实践之间的勾结。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组合,而数字平台在监管内容方面的商业运作机制通常会鼓励上述性别对立或有关性别的对立讨论,尤其是涉及女权主义者时。它们确实为男权叙事铺平了道路,并催生了大量与性别对立的文化套路相关的讨论。
我有两个例子。第一个是有关微博:微博遵循国家监管政策和指导方针,试图通过微博社区协议来巩固其治理,该协议建立了三层自我监管机构5来处理违规行为和惩罚。但举报、过滤、列入黑名单或暂停账户的机制,很大程度上隐藏在众所周知的黑匣子中。当直言不讳的女权主义者身处争议中,而争议本身最初集中在公共场所吸烟问题上时,微博首席执行官王高飞出面提出建议,指导用户通过举报这些账户煽动仇恨和性别歧视,删除那些分享女权主义观点的账户,无论这些帖子的实际内容是什么。该指令显然是由公司负责人发出的,但通常由用户实际执行,以促进内容审核和微博监管的执行。在这些情况下,它似乎承认用户之间存在高度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那些引用反女权主义的人确实得到了平台的认可,甚至在实践中变得更加强大。通过认可这种反女权主义和网络喷子的活动,并消除他们发布暴力言论的障碍,平台确实鼓励了他们的行为。
在另一个案例中,搜索引擎百度故意屏蔽了贬损男性的话语搜索结果,同时保留了其对立项,即厌恶女性的话语。当我在百度搜索了一个厌男词汇“蝈男”,结果显示没有相关内容。而当我尝试搜索另一个厌女术语“蝈女”时,则显示出了一系列的结果。其中置顶的结果是一个知乎帖子,指责女性煽动性别对立。当然,这个结果排列顺序可能是因为我在百度上的数字痕迹(即经常检索性别议题)导致算法把性别对立的内容放在首位推送给了我。尽管搜索“蝈女”产生的结果并非都与这个词本身的厌女含义相关,但这两个搜索结果的不同可以让我们看到:百度本身通过屏蔽贬损男性内容,同时保留厌女内容可见的做法,让我们了解媒体平台是如何操纵其宣传或谴责某些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叙事。
在这次演讲中我从一场争议开始,一位女性单口喜剧演员杨笠因为与拥有大量男性用户的电商平台京东合作而遭到许多男性网友的强烈反对。然后我考虑性别对立的文化套路,以及它如何从有毒的数字男性圈层演变而来,通过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男权倡导联系,最终培育男权运动。我还试图展示中国如何以微名人和影响力文化的实践为中心,试图从数字经济中受益,同时依靠民粹民族主义和草根反精英主义或反资本主义两大道德话语,突出他们的整个议程。最后,简要提及我之前关于国家市场综合体的研究工作:其中社交媒体平台、父权文化、监管和法律、以及媒体用户实践的结合都与男性权利的论述和实践有关——阐释这个综合体如何压制女权主义表达或多样化表达,并滋生、助长仇恨和厌女文化。
由于篇幅、时间以及本人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力量有限,这里仅讨论男性权益运动的一个粗略内容。我甚至不确定是否可以将中国的这种现象称为一场运动,这样称呼可能有些牵强。对于许多倡导男权的著名影响者或流行视频博主来说,松散的男权网络和反女权主义联盟可能无法发展成为一场组织良好、协调一致的运动。他们的追随者群体通常相对较小,大多数在 10 到 20,000 人左右,但单个帖子或视频的评论可能会达到数百万。在中国,男权倡导者无法真正在街头动员任何抗议或示威,这与启发他们的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或韩国的同道兄弟不同。由于数字平台所坚持的利基市场策略,此类宣传的规模和范围也可能受到限制。
但讨论这一现象就是试图证明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国家-市场复合体为此类现象发生所奠定的众多隐性或显性的基础,这都需要更加仔细的拆解。这并不是要将我们在性别和数字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归因于任何男性、女性个体或团体。
我想说,男权倡导是平台政治与意识形态、用户参与和文化价值观相结合的产物,所有这些共同催生了这种真正普遍或暴力的话语,并培育了有毒的数字男性圈层。在倡导男权的话语中,许多活动者并没有解决维持不切实际的标准和任何刻板观念以及男女性别角色的结构,而是倾向于结成联盟来对抗女权主义者和其他女性,并用一些我们认为性别歧视、厌恶女性、恐同、有时甚至是沙文主义的方式采取行动。这就像将男权视为人权一样,显然是挪用了女权主义的话语和策略。围绕男性权利的整个话语被社会资源的权利和政治乐观主义所取代,这确实将整个男权倡导运动与父权资本主义以及我称之为家长式威权主义的东西无缝地缝合在一起。这就是我的全部分享了。非常感谢您的聆听,我欢迎任何评论和反馈。谢谢。
问答讨论
Q:我希望我理解的是正确的,您在演讲中提到在“第二波男权运动”中,他们也在尝试使用包容性的语言。所以,我想知道当他们在网上创建内容时,是否也会推出支持他们的女性?或者,如果不是真正的博主,他们是否有内容谈论女性如何理解可能存在的问题等。我真的很好奇这一点以及他们如何实现这一点。
A:是的,大多数的英语圈男权运动使用包容性的语言。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并不真正单独出现,不只是男性支持这场维权运动,女性也受到欢迎。事实上,我们可以从这些活动人士在网上发布的许多视频中看到,他们还倾向于邀请许多不同的群体为他们发声。所以,“他们”包括女性。我们看到许多更偏向于保守派的女性,她们会同情男权运动。这是一种被仔细包装的类似西方背景下的男性权利的话语。其中一些并没有真正走向那么极端,而是主张以人权原则为中心。我认为非常有趣的事情之一是他们促进了一种对两性都有利的环境。这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方式,就像西方当代男权运动中的一种叙事或策略。一部有争议的纪录片《红色药丸》(The Red Pill)也描述了许多男权活动人士的这种现象。这是相当矛盾的,并不是我们经常想象的那样:一个有着愤怒面孔的男人真正诉诸暴力行动来呼吁男性权利。
Q:您认为哪些人群在中国变得(在“男权运动”中)活跃,以及在美国的情况如何?您认为可以采取哪些策略来反对这种情况,也就是您所说的民粹主义?
A:为了了解这些人的概况,我想说,正如我在西方、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所观察到的那样,与韩国或中国的情况相比是非常不同的。在许多西方背景下,他们中的大多数实际上都有公开活动的公众形象,他们可以走上街头,他们在倡导特定的议题。如果您只是在 YouTube 或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研究男权运动,它会给您一个列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非常公开的。在韩国,它既具有公开性,又有点附加的匿名性,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但在中国,我们通常没有公开的面孔。也许因为它仍然很新,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有着一般模糊的意图,并且没有任何公开言论,或者这可能也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文化并不真正鼓励此类活动。我们不允许在街上进行实际的抗议或示威,但在美国或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我们实际上看到了男权活动家与保守派政党阵营和极右翼分子结成非常强大的联盟甚至是运动,包括我谈到的非自愿独身者和米格道。这些都是知名社群,拥有公众形象,有时甚至得到许多有争议人物的认可。这确实支持了许多极端主义意识形态、阴谋论,但在中国情况却截然不同。我无法真正确定他们的公众面孔,也许就像我提到的两个帐户一样,一个是Morpheus红丸主义,它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不同的帐户,并且在线快速搜索很容易将人们指向这个特定的公众号或中国男权运动的象征,他们基本上只是发布和传播很多有关男权运动的资源的观点角度,就像是中国不同媒体上的教育资源一样。
Q:您了解他们的年龄吗?您所讨论的是哪一个年龄群体?
A: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想根据他们使用的媒体来猜测,他们中的许多人喜欢使用哔哩哔哩,该网站的受众群体更加年轻,年龄在 20 多岁或 30 岁出头,其中许多人沉迷于日本动漫和漫画,也是这个网站起初的文化背景。所以,这是我的猜测之一。另外,在他们传播的一些视频中,你会真实地看到讨论这些问题的人,从我看到的图像来看,他们中的许多人看起来 30 多岁,甚至更年轻。通常我会相信这是一个更年轻的群体。
Q:您刚刚也讲到在中国有很多男权主义者或者说 incel 男,他们经常觉得中国互联网上的男女对立是境外势力挑起的,但是同时他们又比较追随埃隆·马斯克这样厌女的国外精英阶级,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民粹主义,因为这挺双标的。而且像马斯克这种明确发表过厌女言论的人都能成为名人,很可能因为他手里掌握着社交媒体。并且在刚刚的美国大选里,特朗普也当选了,美国女性的堕胎权又受到了威胁。其实有很多中国女性还是比较关注美国大选的,因为在我们自己国家出一个女性领导人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连美国的女性领导人都竞选失败了,很多中国女性挺失望的。您觉得这是不是美国乃至全球的女权主义的一个倒退?我们要如何应对这种精英阶级,比如说掌握着社交媒体的人和统治阶级领导的越来越浓的这样一个厌女氛围?
A:这个问题非常好,也非常大。首先我觉得你的观察是对的,全世界不管是在哪个国家都面临一个巨大的右倾转向,这个当然不仅仅是影响到政治层面,还有社会生活文化。选举是这整个右倾的一个侧面,但我并不认为说这就是全世界女权运动的一个倒退。可能我们暂时处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情境下,你感觉到的声浪或者你能体会到的这种明显的政治焦虑,会让你觉得女权运动逐渐失去了阵地,包括美国最高法院对堕胎权的推翻,以及全球其他各个国家,比如说伊拉克等地区的妇女权益受到了很大的威胁。但我还是认为尽管在这样一个极其艰难的局面下,世界各地的女权组织和女权主义者们还是有在做各种各样的努力。最近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的学者谭佳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缓慢抵抗》6,她利用研究环境问题里的一个概念,描述威权主义国家下女权主义的反抗是怎样的形式,她把这个命名为“slow resistance”,即很缓慢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有时候甚至不可见,它可能不是发生在一些显性的社交媒体,甚至可以有公众面孔(public face)的地方,可能更多呈现为社区当中的互助或者说一些不在公众视野范围内的微小改变。我自己比较赞同这是我们会面临的一种境遇,我们可能需要调整女权主义运动策略,同时去思考、花时间去沉淀,什么样的策略、什么样的方式更能应对当下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不能丧失信心,因为女权运动发展本身就是走一步退两步,但不能因为这种情况,我们就放弃了希望。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任何一个权力,无论男性女性,其实都是建立在前人不停的努力下,所以我不觉得这是女权运动倒退的表现,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做的很微小的一些事情,可以一同度过这样一个局面。
Q:我也对中国女权运动及其竞争对手男权运动进行了一些研究。所以,我个人很好奇您对中国激进女权主义的看法,比如中国的“激进女权”,就像是一种“激女团体”。在这样一个充满性别敌对叙事的文化背景下,有哪些有效的策略可以用来抵消和促进性别平等的讨论空间?
A: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是在问我对所谓极端女权主义以及对抗对她们发出敌意的策略的看法吗?首先,我认为即使是所谓的极端女权主义或“激女”团体,仍然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范围,涵盖各种意识形态。更深入地说,这些女性也有一些共同的目标和追求。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看到性别对立成为一种文化套路,专门针对这一群自称为“激女”、极端女权主义或激进女权主义,或源于第二波女权主义的拥护分离主义意识形态的网络活动人士,我不认为网络空间中真的会出现“激女”想要推动的那种非常理性、非常和平的讨论。我对数字媒体尤其是中国的整体公众讨论并不十分乐观,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空间:这里的任何公开讨论都需要保障绝对的政治正确,而女权主义已经被淘汰,无论你是极端女权主义者还是偏向保守或温和的女权主义者。
我不认为数字媒体可以提供空间进行真正理性地讨论这些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发现在某些方面我们可能并不仍然想坚持促进数字空间或数字行动主义。相反,这可能是重新思考或重新配置我们建立的社会性的好时机。人与人之间,我们也可以开始以一种真正具有人际联系的方式重新思考事物,而无需诉诸数字媒体。虽然我正在研究数字行动主义,但我不得不说,在这种背景下,尤其是现在的中国,有很多限制以及更加威权。那么,这也回到了上一个问题,当时我提到谭佳关于“缓慢抵抗”的想法。这并不是要在数字媒体上提供新的策略,而是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旧媒介中的人性和社会性如何帮助我们推进我们的政治议程。而这其实也有很多方面的实践,当我研究数字活动家文化时,我了解到有些人开始进行更多的面对面实践,例如建立一种共生空间,并且它就是真实的空间,无需在网上进行更多讨论和宣传,而是在实际上开始培育社会空间。还有其他类似的女性团体在组织着不同类型的活动。事实上,邀请人们聚在一起,参加观鸟、徒步旅行等活动,但这是一种非常具体的建立联系和联盟的方式。这不仅仅是一场我们努力赢得的话语战,我认为这从根本上回到了如何以更加缓慢和传统的方式建立联系、联盟和团结的问题。
- 编者注:原话为“男人不光美好,还特别神秘,就是你永远也猜不透他那小脑瓜里,到底在想一些什么。就是他明明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 ↩︎
- 译者注:文化套路(cultural trope)指用过度简化的方式去描述或代表某种文化。 ↩︎
- 编者注:男人自行之路(Men Going Their Own Way),简称米格道(MGTOW),是一场以网站、论坛和社交媒体等虚拟社区为平台、以匿名男性用户为主体、倡导男性解放和自我所有权为口号的男性主义运动,致力于告诫男人杜绝与女人发生严肃认真的恋爱关系,特别是婚姻关系。 ↩︎
- 作者注:作者在追溯的过程中发现了2017年的一些文字讨论。 ↩︎
- 译者注:三层自我监管机构指用户自律、平台审核、第三方监督。 ↩︎
- 编者注:Tan, Jia. 2024. “Slow resistance: Feminist and queer activism in ‘illiberal’ contexts.”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
讲者介绍
廖雪婷
Sara Li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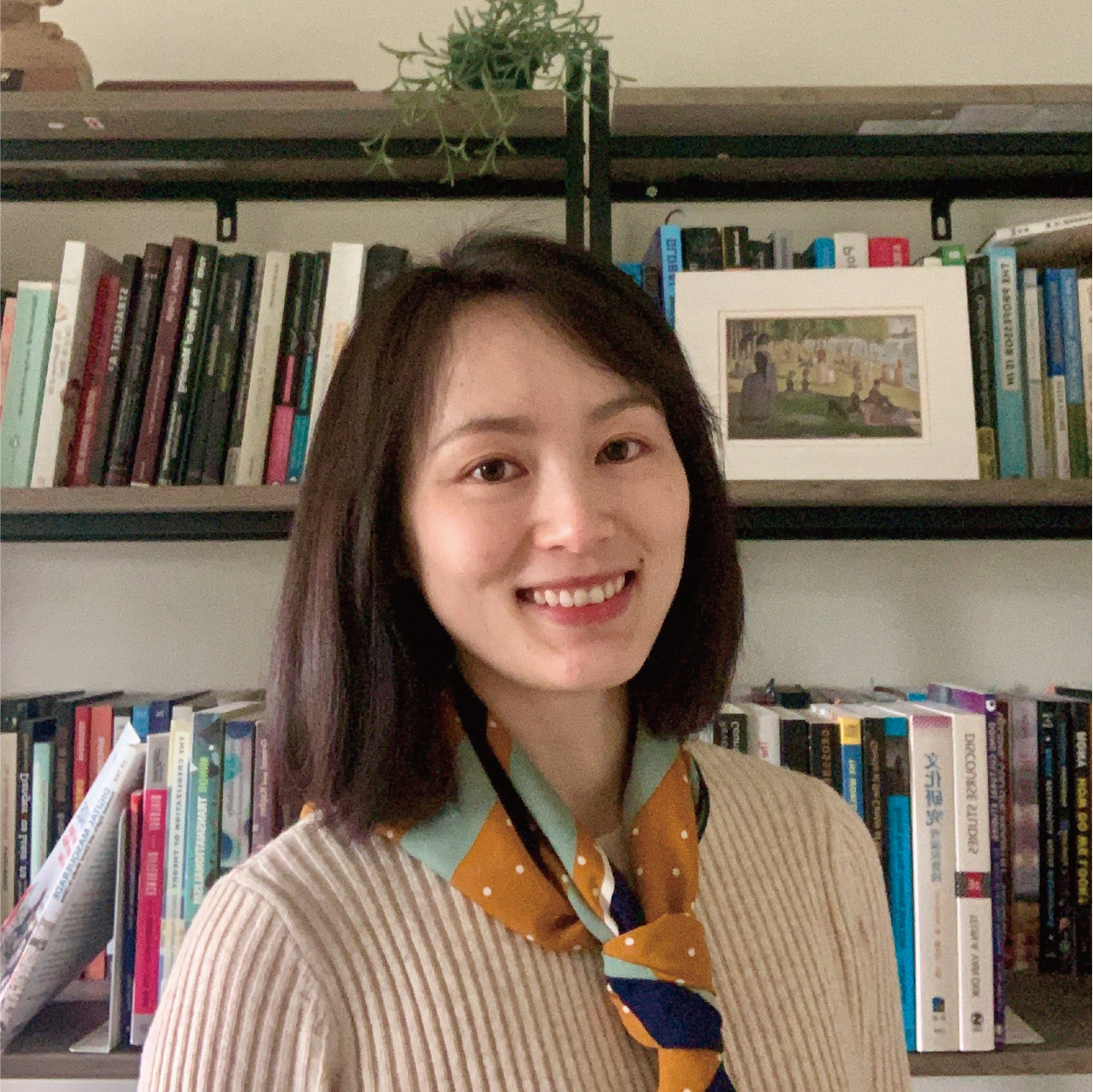
简介:廖雪婷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媒介研究专业的助理教授。她是一名媒体学者和女权主义者,研究数字媒体、女权主义、全球化和东亚流行文化的交叉领域。她目前正在从事数字女权主义运动以及中国厌女文化的理论化与写作工作。
